庄语乐︱宋代历史是被“塑造”出来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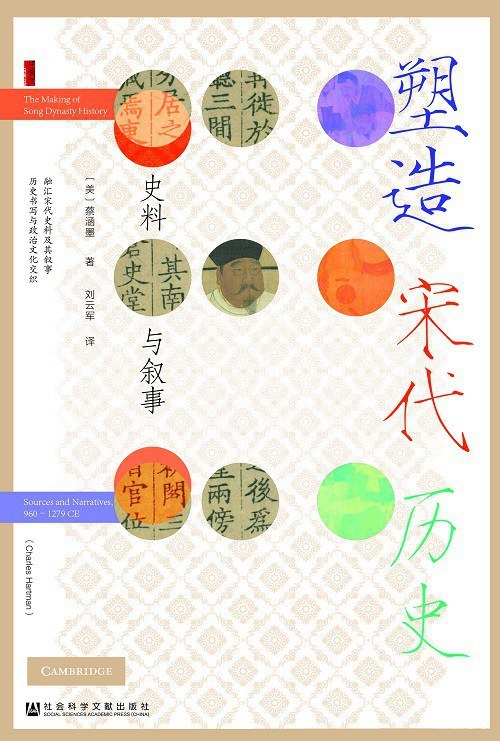
《塑造宋代历史:史料与叙事》,[美]蔡涵墨著,刘云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644页,119.00元
美国学者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的新著《塑造宋代历史:史料与叙事》中译本新近问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2月版,刘云军译;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Sources and Narratives, 960-1279 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下文简称“蔡著”或“本书”,征引中文版内容,以夹注“第某页”形式标明页码,不再单独出注)。本书主要讨论了宋史史料与史料文本的叙事问题,作为海外学界最近研究宋代史学史与政治、思想史的力作,“是第一本参考当代解构主义理论来分析宋朝史学主要修辞特征的重要研究成果”(导论,第4页)。
蔡著开宗明义,以导论“走向动态的宋代史学”阐明著述思路,总论全书内容,将宋代历史著作视为一种“动态”创作过程,从而提出“活的史学”的概念,并给出“探讨这些特征如何影响现存的宋代历史记录”(第8页)的目标。导论以外本书共设十一章,分为两部分,其中一至五章为“史料”部分,六至十一章为“叙事”部分。
本书“史料”部分五章,分别探讨《宋会要》、李焘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下文简称《长编》)、李心传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文简称《要录》)、道学史家,以及元修《宋史》;总的来说,在这些文本的“史料”属性之外,作者更主要将其视作一种“修辞”或政治隐喻。
“叙事”部分六章,主要阐述了宋代的政治“故事”、历史叙事以及由此产生的“宏寓”概念(第六至七章);并分论“宏寓”的三个主题:“仁政”(第八章)、“神化太祖”(第九章)、“奸邪谱系”(第十章);最后以“宋代历史的节奏”(第十一章)收尾;这部分在“史料”之上,进一步将一切宋史史料视作一种“塑造”,历史编纂作为政治“工具”,“除了谄媚皇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力量推动实录中叙事的形成”(导论,第22页),也即,宋史史料对作者而言主要是“宏寓”,“宏寓”又是由“谄媚皇室”和“共治工具”两大要素组成的。
本书最吸引眼球的,自然是其书名“塑造(the making of)宋代历史”,这一论点在本书的“叙事”部分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但是,宋代历史真的是被“塑造”出来的吗?这就需要结合本书主要是“叙事”部分的具体论证结构,点对点进行回答。
“故事”的理解和“仁政”的分析
在作者的眼中,特定的宋代史料是特定史家为了传递自身政治观点,而组合出的一种“文本”。作者抓住了“故事”这个关键词,进行了集中分析。但作者的分析往往有其问题,特别是在“史料”部分对“故事”得出了错误理解,并由此干扰了“叙事”部分的分析。
例如在第一章里,作者说“编修会要的目的并不是将其作为历史记录,而是作为‘故事’的参考文献集”(35页),可是,作为历史记录和作为“故事”的参考并不矛盾,会要为什么不能是历史记录呢?作者说“宋代学者大体上没有将会要视为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档案’”(36页),却没有给出“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档案”这一含糊概念的定义,也不曾提供宋代学者不将会要视为“历史档案”的证据。这些逻辑上的不通之处,作者完全没有给出解答,只是默认了《宋会要》是为了创造“故事”,影响政治,反倒说“会要尽管作为历史作品有益”(45页),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作者自认为抓住了“会要”和“故事”的联系,由此对《太平故事》展开了一段似是而非的分析。在第一章中,作者提出《太平故事》是《国朝会要》的节本, “1044年四月,王洙进呈了第一部会要——150卷的《国朝会要》;五个月后,即九月,王洙又进呈了20卷的《太平故事》。本书第六章将更详细地研究《太平故事》,该书是《国朝会要》的节本,是小部头著作”(37页),在第六章中,作者又说“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见,《太平故事》与宋朝的首部会要关系密切”(343页)。作者巧妙地将两点放在相隔甚远的不同章节中,但始终都没有给出《太平故事》是《会要》节本的有力证据。唯一的联系,就是二者皆由王洙上呈。但实际上,《太平故事》是由富弼领修并上呈的,王洙在史院任职,虽然参与了修撰,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部书最终由他上呈。作者在后文中,又以“由王洙率领的编撰小组,以富弼的名义进呈了这部作品”(344页)找补,可这样的找补已经显得有些左支右绌。
同时,《太平故事》与《会要》的关系并非不能考察。南宋俗书《太平宝训政事纪年》曾大面积引录《太平故事》原文,可以发现,《太平故事》与今本《会要》根本不可能存在源流关系。不仅呈现形式相差很大,文本更是不存在重合之处。《太平故事》不可能是《会要》的节本。其实,如果作者真的对《太平故事》进行过研究,很容易发现此书体例近似石介《三朝圣政录》。事实上,《太平故事》即有别名曰《三朝政要》和《三朝圣政录》。同时,编者对书中每件史事加上了自己的评语,即“臣弼等释曰”,这些都是可用以判断《太平故事》体例与性质的证据,惜乎作者都没有提及。
当然,作者也确实留意到了富弼在《太平故事》中的重要性,却对富弼的用意同样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作者认为“富弼的《太平故事》强调了儒家‘仁’的美德是宋初治国的基本性质”(381页),但原文是“推是仁心而临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宋史全文》卷二),说的是宋太祖平定全国,而非“宋初治国的基本性质”。
在这一错误判断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说“罗从彦甚至将仁宗统治时期的成功和国家昌盛归因于《太平故事》确定的这些政策。但是,对于现代历史学家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太平故事》的选择和解释成为界定祖宗成就的史学基础”(344页),可罗从彦说的是“(仁宗)能为太平天子四十二年,民到于今称之,以德意存焉故也。况德意既孚于民,而纪纲又明,则其遗后代宜如何耶!此弼之所以奋然欲追祖宗、思刬革也”(《遵尧录》卷四),上述诸端,指的是富弼的撰述意图,却无一语提及“归因于《太平故事》确定的这些政策”,而作者所谓“成为界定祖宗成就的史学基础”的论据,竟然只是罗从彦、吕源二人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了《太平故事》的条目,难道在作者眼中,宋代史学的基础就如此薄弱吗?其实,许振兴、李裕民等学者都对《太平故事》进行过一些研究,分别收录在《饶学与华学:第二届饶宗颐与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与《富弼家族墓志研究论文集》中,许氏论文更是对《太平故事》的性质作出了判断,并对遗文进行了初步辑录。本书作者对这些论著无一征引,虽然可能只是搜讨不及。
以上可见作者在“史料”部分即对“故事”的理解产生严重偏差。到了“叙事”部分,这一理解偏差自然会引起更加荒谬的推论。作者先是提出了宋代的“故事”与“祖宗之法”引起的独特“历史叙事”(第六章),但是作者对这段时期的史料进行了似是而非的解读,例如作者提出“在皇帝经筵上‘进故事’的做法,始于范祖禹在1087年‘进故事’,而这些早期例子主要限于汉唐‘故事’”(335-336页),但经筵进故事早在仁宗朝就已有大量事例,王安石等人侍讲时每每“寻故事”,以“祖宗之意”为说,皆有记载,对此,朱维铮、姜鹏等学者早就有详尽的考察(《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作者无一提及。
同样,作者对“祖宗”的概念,同样也存在认识的偏差。例如,作者引用曹家齐的研究,称“随着王朝发展,祖宗的定义已经超越了实际的宋朝开国者太祖与太宗。殆至北宋灭亡,北宋已经包括真宗与仁宗,通常也包括英宗——简而言之,即神宗之前的所有北宋皇帝”(381-382页),可曹氏的结论恰恰是北宋每代皇帝都将前朝加入“祖宗”之中,并未提及“北宋灭亡”和“神宗之前”的断限(《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作者自己不能论证哲、徽、钦三朝不以神宗为“祖宗”,反而躲在前人研究之后闪烁其词,得出的结论恐怕难以让人信服。
而后,作者又提出了“宏寓”概念(第七章)。作者认为,宋代历史上的特定重大事件,引发了“历史书写的修改运动”(387页),从而形成了一种塑造了今日所见宋史面貌的“叙事”,所谓“宏寓”,就是这样一种将历史“事件安排成主观叙事”(387页)的概念。作者将“宏寓”分解为三大主题,分别为“仁政之国”、“神化太祖”与“奸邪谱系”(380页)。接下来的第八、九、十章,就依次考察了这三个主题。
所谓“仁政之国”的宏寓,即认为宋代的历史叙述极度抬高“仁政”的地位,从而塑造了一种“庆历—元祐的政治价值轴心”(426页)。不过作者在论述中却刻意延后“仁政”概念的出现时间、曲解宋代史料中“仁政”的地位,如作者认为“‘仁政’一词首先出现在《长编》1029年的记事中,但在1042年以后才被宋人普遍使用”(441页),并在注释中解释“《长编》在962年正月的条目中出现了‘仁政’,但是,李焘插入《长编》的这一条目来自《三朝宝训》和《太平故事》,两书都是庆历时期的文本……这些事件的后来版本并没有提到‘仁’”(483页),可是《长编》原注作“伦传不载其年,《故事》称元年,《宝训》称二年”(《长编》卷三),可知此则史料源出沈(义)伦本传,最早可能在真宗朝修《两朝国史》时已经存在,亦可能是天圣八年(1030)《三朝国史》中增加,绝不会晚到“庆历时期”。另外,《三朝宝训》不是庆历时期的文本,而是明道二年(1033)奏进。总之,这段论述忽略了“伦传”二字,又故意给《宝训》系上错误的年代,从而达到延后“仁政”概念出现时间的效果,来满足自己的建构。又比如在论述“神化太祖”时,作者说“早在1085年,司马光就呼吁回归祖宗之法,明确称祖宗只是太祖和太宗”(484页),可是遍检史料,根本找不到司马光说过“祖宗只是太祖和太宗”。
此外,作者还过度抬高某些孤证和特定史籍的意义,例如作者极度重视《遵尧录》的历史叙述,可此书在宋代历史上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也就导致论述不尽可信。事实上,本书论及所谓“庆历—元祐的政治价值轴心”,讨论深度也没有超过所引邓小南、曹家齐的研究(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曹家齐《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祐之治”新论》),更何况,方诚峰等人的更多研究也被作者忽略了(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曹家齐《“爱元祐”与“遵嘉祐”——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
“神化”和“奸邪”:有缺陷的文献实证研究
相较对“故事”和“仁政”的演绎性理解,“神化太祖”一章是最“实证主义”的研究。作者认为,受南宋初年政局影响,宋太祖在此时被塑造成了一位最值得效法的圣君,亦即“宋朝中兴的核心形象”(480页)。作者以陈桥兵变以及杯酒释兵权两个“故事”的叙述为个案,认为宋太祖在这两件史事中的作用,都在南宋的历史书写中被“神化”了。
然而,作者的两个个案考察都不能完全成立。
对陈桥兵变中约束将士的记载,《涑水记闻》与《长编》并不相同,前者主张宋太祖自行约束,后者正文则采宋太祖、太宗及赵普共同定策之说,作者由此展开论述:
李焘的注表明:(1)980年的“(太祖)旧录”记载了太祖与士兵的协议,即不洗劫都城,这完全是太祖的主动行为;(2)999年的“(太祖)新录”将这一想法归于太宗;(3)1030年的《三朝国史》详细记载了太宗和赵普了解士兵支持太祖称帝的计划……无论这个版本(《涑水记闻》中太祖自行约束)何时出现,又是如何形成的,它都与官方历史《三朝国史》的记载相悖,因此必然是有意省略了太宗的角色。12世纪30年代对太祖的新关注,使他在王朝建立过程中扮演新的角色……(范冲受高宗旨意篡改《涑水记闻》)由此产生的今本《涑水记闻》不仅在陈桥兵变一事上,而且在整本书中都强调了太祖而不是太宗所起的作用。其结果是一场极端的历史修订,认为政治价值观从太祖经由庆历和元祐,直接传承到高宗和中兴时期。(以上引自456-457页)
也就是说,作者认为(1)太祖兵变自行约束将士属于一种刻意的塑造,而(2)今本《涑水记闻》是在皇帝授意下对历史进行“极端”篡改的产物。
(1)的原因是:《涑水记闻》与《三朝国史》的记载相悖,所以一定是南宋形成的。但是,李焘的注文也说明,更早成书的《太祖旧录》所记载的原始版本,即太祖自行约束,这显然不是南宋形成;其次,王禹偁《建隆遗事》成书极早,明言太祖自行约束,又有“上初自陈桥即帝位,进兵入城,人先报曰:‘点检上时官为点检已作天子归矣!’时后寝未兴,闻报,安卧不答,晋王辈皆惊跃奔马出迎”(转引自《邵氏闻见录》)的记载,太宗“惊跃奔马出迎”,可见太宗根本未随军出征,根本无从定策;其实,以当时太宗官职,并无理由随军出征,学者多有提及(如顾宏义《王禹偁〈建隆遗事〉考》),作者则未有只言片语提及这点。
(2)则默认了今本《涑水记闻》并非司马光而作,而是范冲篡改的产物,证据是:“范冲为皇权和赵鼎的政治利益行事,他比司马光更有权威和动力来进行这些改变。从本质上说,高宗准许范冲使用司马光的轶事以避开君主自己的官方历史。”(457页)可是众所周知,范冲是整理手稿,而且明言不敢进行篡改,“不敢私”(《要录》卷一〇四),同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皇帝授意其修改。邓广铭明确指出:范冲对司马光的这份手稿,只有在有根据、有把握的情况下才敢于正误、补阙;对其中的记事重复而文字稍有详略不同的,尽量两存其说而不予删除(《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这点已是学界共识。作者没有直接回应此点,却称“从本质上说”,恐怕代表了作者无法“从史料上说”的本质。
在这样偏颇的论述之后,作者已经默认宋太祖“自行约束”是一种对他“神化”的记载。而李焘此时则扮演了公正的法官角色。对《长编》不采用“自行约束”之说,作者论述说:“李焘很了解这部书(《涑水记闻》),并经常使用它。但是,李焘的陈桥兵变叙事完全忽略了司马光的版本;通读起来,他的叙事和注文批评了当前的太祖独角戏的情况。”(458页)
但实际上,李焘的陈桥兵变叙事完全承袭了《涑水记闻》的框架,又比如约束将士的言语,《涑水记闻》称“事定之日当厚赉汝,不然,当诛汝”,《长编》则谓“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显然是后者承袭了前者,不可能如作者所说“完全忽略”;此外,李焘注文称“《旧录》禁剽劫都城,实太祖自行约束,初无纳说者。今从《新录》”,读不出“批评当前的太祖独角戏的情况”之意。实际上,有学者认为这种表述是官方抬高太宗地位叙述下被迫采取的手段(吴铮强《官家的心事》),是在暗示“太祖独角戏”才是历史的真实,这种情况其实更符合逻辑。然而,作者没有引出这条注文,却大谈“批评了当前情况”,恐怕并非规范的学术论述。
对杯酒释兵权的记载,作者则将大量笔墨放在《涑水记闻》上,认为是《涑水记闻》塑造了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作者又提及其中一处“以散官就第”的错误,认为“司马光本人不太可能犯这样基础性的历史错误”(477-478页),从而称“考虑到《涑水记闻》的编纂历史,我们无法得知究竟是谁把现存‘司马光’的杯酒释兵权叙事拼接在一起……正如李焘表明的那样,第一段文字是作为序添加的,以构建主要的叙事,这种拼接很可能发生在12世纪30年代的某个时候”(478页)。
需要澄清的是,作者称“正如李焘表明的那样,第一段文字是作为序添加的,以构建主要的叙事”,但李焘从来没有类似表述。
尽管《涑水记闻》确实出现了史实错误,但所谓“记闻”指的就是“记录听闻”,这段文字后明明写了出处“始平公云”,即这条记载乃从庞籍处听来,口述存在偏差本是情理之中的事,作者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以“司马光不太可能犯这样基础性的历史错误”和打引号的“司马光”来暗示这段记载是后人捏造的,并不妥当。
在这样的错误论述之上,作者又称“司马光关于杯酒释兵权的叙事在《涑水记闻》之外第一次被接受,见于《邵氏闻见录》”(478页),但如若这段记载真是“12世纪30年代”被人“拼接”成的,此时已经去世的邵伯温又怎么将其写进《邵氏闻见录》?其实若把今本《涑水记闻》与《邵氏闻见录》对比,就会发现二者文字几乎一模一样,并不符合口述史料的流传规律;进而,《邵氏闻见录》除此卷外的全书,并无一次引用《涑水记闻》,足证邵伯温并未见到《涑水记闻》,此处抄袭《涑水记闻》,也就大概率非邵伯温所为;最后,《邵氏闻见录》本卷第十四条记载同样提到“杯酒释兵权”,人物、情节和《涑水记闻》完全不同。一书之中显然不会出现打自己脸的情况,足证并非《邵氏闻见录》接受了《涑水记闻》的叙事,而是后世有人抄袭《涑水记闻》时,将其混入《邵氏闻见录》中。
今人关于杯酒释兵权,已经有很多研究。其中,顾吉辰《关于宋初“杯酒释兵权”的几个问题》一文最为精当,史事流变基本可以定论。作者只参考成文极早的聂崇岐《论宋太祖收兵权》以及邓小南《祖宗之法》中的讨论,就自顾自地大谈“宏寓”,似乎史事考证的能否成立,已不在作者关心的范畴了。
同样的刻意忽略前人研究以满足己说的情况,还见于作者对《中兴小历》的讨论。作者称“有学者认为,现存的两种高宗早期史书《中兴小历》和新近发现的《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是熊克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不过,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这两部著作并不相同”(499页),对这一观点,作者只引用了周立志的一篇论文,又举出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将这两本书分列的情况,作为二者并不为一书的证据。
但事实上,学界普遍观点是今本《小历》和《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并非熊克原书,二书属于繁、简本关系,而《要录》引用的《小历》远非今本《小历》。关于这点,温志拔、黄露等人均有专文发表,蔡涵墨不可能不知,而最新研究表明,《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是《小历》遭禁以后,民间书贾在《小历》原书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另一种史书(高纪春《〈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关系再研究》)。作者只引一篇论文,并用《小历》遭禁后的《纲目备要》论证《小历》与《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不同,无论如何恐怕都难以令人信服。
至于之后的“奸邪谱系”,其实就是作者在前著《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中华书局,2016年初版;2024年再版)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道学对南宋历史的影响,作者认为《宋史》构建起了一个“奸臣谱系”,而其中的书写是具有极高“道学敏感性”的(511页)。不过,元修《宋史》的主观因素似乎被过度抬高了。例如作者认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的‘平均标准’传记在中华书局版《宋史》中约占10页。例如,《赵普传》10页,《王旦传》10页,《韩琦传》11页,《富弼传》9页。任何篇幅超过这个长度的传记,要么表明元朝编者们特别重视这个人,要么表明他们是在利用此人的传记来强调传主日常生活之外的一些更宏大的观点”(294页),但这样的“页数统计法”是极不科学的,作者不规定“重要”的标准(如官衔、亲属关系),也不限定人物传记的门类归属(如文武之分),只举出四个北宋前中期的人物,就下了“重要政治人物平均10页”的判断。时代先后、传记材料多少等更直接关系到篇幅的因素都被直接忽略了。最关键的是,作者无视《宋史》基本保留北宋《国史》面貌的事实,将篇幅长短完全归因于“元朝编者”的“宏寓”追求,而忽略了史源学和编纂学的常识。若元修《宋史》真能如此细致地照顾到每个人物的篇幅长短,两年多时间如何修成,又怎至于粗疏劣史之讥?赵翼早有“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的论断(《廿二史札记》卷二三《宋史多国史原本》),蔡氏通篇论述竟至全然不顾。
就是在这样的论证之后,作者用“宋代历史的节奏”(第十二章)收束了全书,尽管所谓“节奏”只是用黄震的一段话,去和当时的政治局势对应。可以看出,作者口中“塑造宋代历史”的逻辑十分简单,只要是“文本”,就是“塑造”,至于为何要“塑造”,只需用当时的政治背景就可以解答。例如讨论南宋出现“神化太祖”的政治原因,作者说“只要太宗的继承人控制皇权,就没有提升太祖地位并使其超越太宗的政治动力”(449页),可这明明是宋史学者的基础共识,本不需要洋洋洒洒数万言来论证,而这样以具有普适性的概念解释特定历史事件的做法,又从本质上不具备任何解释力。
何以塑造本书作者?
行文至此,本书之谬误已庶几明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现象,大抵还要仿效作者对宋代史家以“塑造”诛心的手法,对作者本人进行一些剖析。
译者在翻译本书时,将原本简短的第七章替换为了作者发表在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上的长篇论文(译后记,623页)。透过本章的表述,读者也得以一窥作者的心境。
蔡涵墨教授并非宋史专业出身,而是以唐代文学研究起家(Han Yü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正如中国读者们更多通过他对秦桧的研究了解到这位学者,作者本人也通过这一研究进入了宋代文献学的空间。他长于理论的同事的评价则让他发现,自己“已不知不觉接受了语言学的转向”(361页)。作者自己也承认,自己的研究是“语言学转向”,也就是“后现代化”的。
不过,作者似乎不愿意接受“后现代史学”的定位,他坚持宣称“我的学术研究从未追随任何清晰可辨的潮流,我对后现代主义也一无所知”,“后现代主义的术语令人费解,其复杂的心理学立场也令人反感”(361页)。然而,从作者的用语来看,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术语”运用之熟练,显然超出了“费解”的程度,他在全书中使用了“历史书写(historiographical/historical writing)”八十余次、“叙事(narrative)”三百六十四次、“文本(text)”三百四十八次、“建构(construction)”“重构(reconstruction)”与“解构(deconstruction)”共五十余次。作为对比,被作者置于“宏寓”概念中极高地位的“仁政”一词,在数百万言的《长编》中总共也才出现了不过三十次。对海登·怀特等学者的反复引用,以及“元叙事(metanarrative)”这样极富“后现代主义”色彩术语的高频出现,无不展示出作者的后现代史学倾向。
尽管在自序中表示“《塑造宋代历史》这个书名,并不意味着我信奉更激进的解构主义”(中文版序,第3页),作者也没有在言语之外采取实际反对“激进的解构主义”的行动。他也毫不避讳谈及自己“阅读历史文本不是去决定哪些事实可信,而是去探查原初的史学建构与其后的事实重建者二者的轨迹”(363页)。然而史事本有真伪,史家也不能回避判断记载的可信与否。正如本文上一节中提到的,作者在讨论陈桥兵变史事时,忽略史料、逻辑共同指向的“自行约束”之说,把历史解释一股脑地抛给写作者的主观性,却恰恰是忽略了历史本身的面貌。
这种谬误并非没有前车之鉴。同样作为美国史学家的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 Rogers)早在六十年前讨论苻坚与淝水之战时(The Chronicle of Fu Chien: A Case of Exemplar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就运用后现代的分析方法,对《晋书》中的《苻坚载记》进行了系统的解构。他认为,苻坚与淝水之战的故事,是初唐史臣为了塑造正统、规谏帝王,捏造出的“神话和文学描写”,这种结论恰似作者对宋代史料的认识。不过,孙卫国早就以长文系统驳斥了这种看法(《淝水之战:初唐史家们的虚构?——对迈克尔·罗杰斯用后现代方法解构中国官修正史个案的解构》),指出其论史方法虽新颖,但结论却是荒诞不经的。其实,无论是罗杰斯还是蔡涵墨,都是在未能充分理解历史编纂逻辑的前提下,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贸然进入历史书写的范畴,从而犯下过度迷信个人主观因素的过失;正如淝水之战并不是初唐史家们的向壁虚造,宋代历史也不是当时史家的有意“塑造”。
过度“后现代”的史观之外,作者在其自身文化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隔膜,也为他解读宋代历史带来了更多困难。作者认为,李心传写作历史是为了“将其研究成果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治国方略来源”(164页),可征引的史料,说的却是“然则是编也,或可以备汗青之采摭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序》)史料与作者的解读并不能对应,这是因为作者在读到史料之前,就已经预想史家修史是为了影响政治。这种将宋代士大夫视作一种现代化的政客的观点,不当抬高了宋代士大夫对干预政治的追求,却恰恰忽视了他们真实的精神追求。在李心传“或可以备汗青之采摭乎”的发问之前,还有一段自白:
“近世李庄简作《小史》,秦丞相闻之,为兴大狱,李公一家,尽就流窜,此往事之明戒也,子其虑哉!”心传矍然而止。未几,权臣殛死,始欲次比其书,会有旨给札,上心传所著《高庙系年》,铅椠纷然,事遂中辍。既而自念曰:“此非为已之学也。”乃取旧编束之高阁,而熟复乎圣经贤传之书。又念前所未录者尚数百条,不忍弃也,萃而次之,谓之乙集。
撰写《朝野杂记·乙集》的心路历程之坎坷,由斯可见。对政治变局中的文人士大夫来说,撰史并不是干预政治的利器,却可能招致大祸。对他们来说,“圣经贤传之书”才是值得长久追求的“为己之学”。李心传不忍史事遗落无闻,愤而著《要录》《朝野杂记》,自是立言以传不朽的壮举,可将其说成是为了干预政治,即便赋予这些修史行为极高的价值,恐怕也辜负了其最初的本意。
总而言之,本书对“塑造宋代历史”的论证,无论从逻辑、结构还是个案和细节上,恐怕都不能成立。这些“塑造”,又往往都是作者本人的学术进路、理论观点、文化背景等因素在宋代历史领域的投射。可以说,这是一种充满“偏见”的“一厢情愿”的理解。真正的宋代历史,终究并不是被“塑造”出来的。